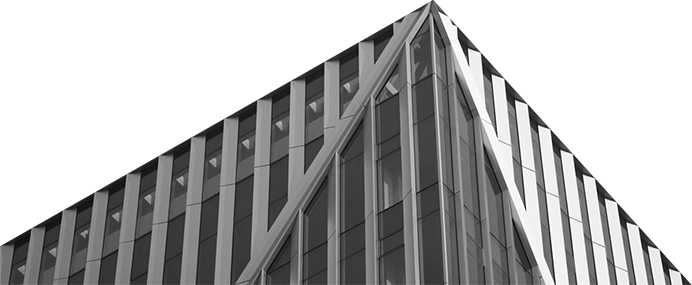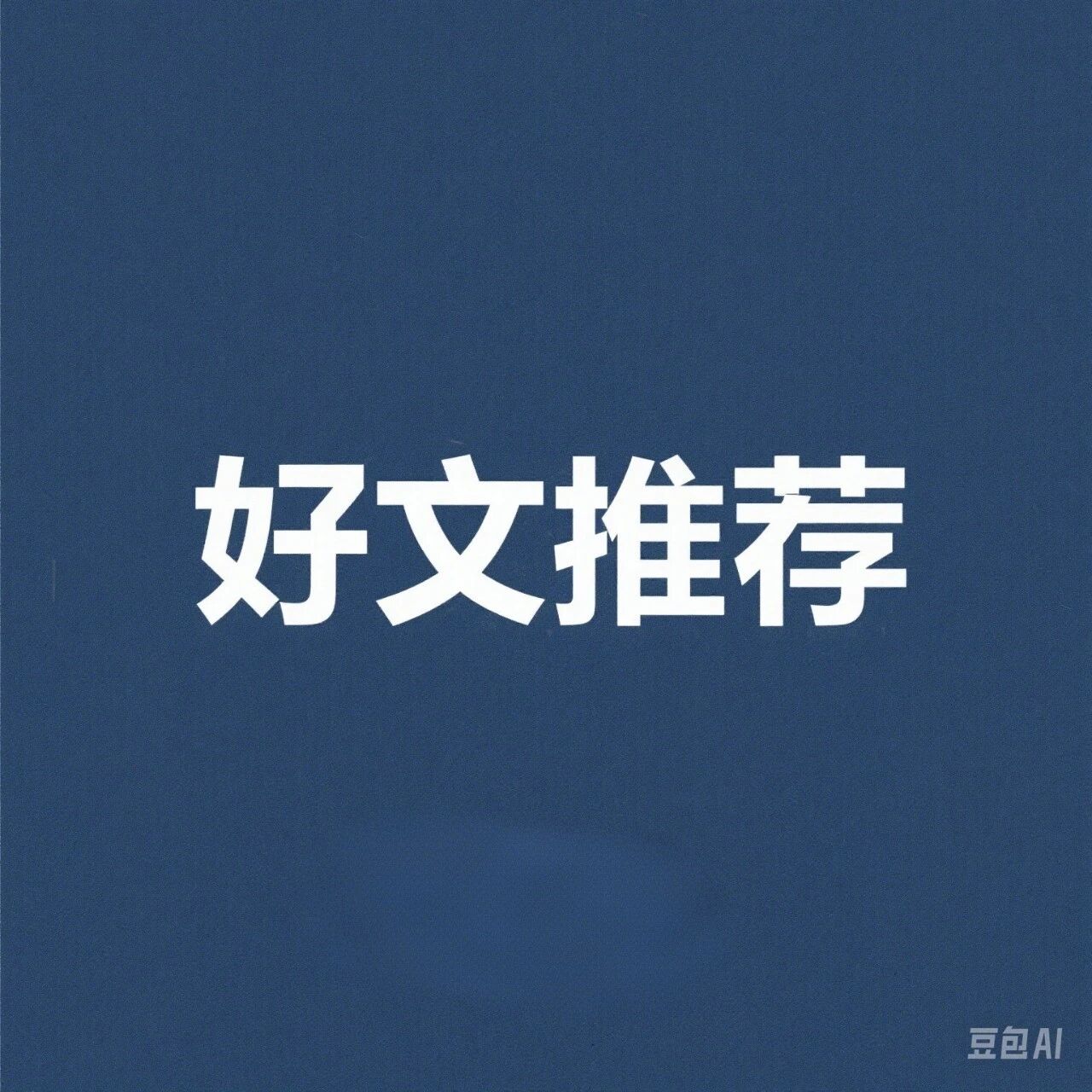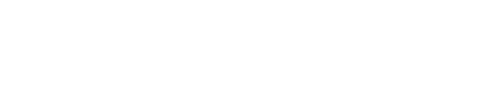
智合商学ZHIHESHANGXUE
为变革型企业提供管理创新关键能力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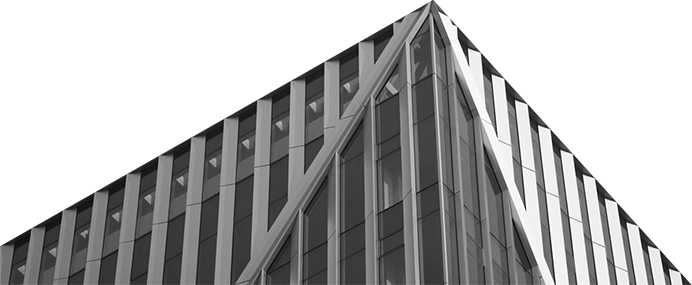
2025 年,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完成了一次关键的工商变更 —— 注册资本从约 580.8 亿元增至 638.9 亿元,增幅达 10%。这次变更中,一个细节引发广泛关注:华为工会委员会的认缴出资额增至 635.5 亿元,持股比例从 99.42% 升至 99.48%,而任正非的出资额始终维持在 3.35 亿元,持股比例却从 0.58% 降至 0.52%。
看似微小的数字变化,实则是华为数十年股权架构演进的缩影。从 1987 年创业时的六人合伙,到如今 “创始人持股不足 1% 却掌控全局” 的独特模式,华为的股权设计不仅是企业治理的经典案例,更藏着其保持凝聚力与创新力的核心密码。
华为股权架构的四十年演进:从 “均分” 到 “共享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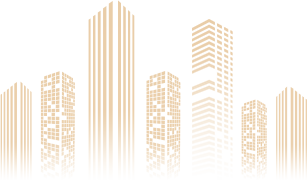

华为的股权之路,始终围绕 “如何让更多人参与企业发展” 展开,每一个阶段的调整,都贴合当时的业务需求与组织规模。
01
初创期:六人合伙的 “均等起点”
1987 年 9 月,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成立时,注册资本仅 2 万元,由任正非与另外五位合伙人按均等比例持有股份。这种 “平均分配” 的合伙制,是创业初期的朴素选择 —— 大家共担风险、均分利益,契合小企业 “活下去” 的核心目标。
但随着业务逐渐起步,五位合伙人对华为的发展方向产生分歧,最终通过赔偿方式陆续退出。这一变化并非 “断裂”,反而为华为后续的股权创新铺路:企业从 “多人共治” 转向 “以任正非为核心” 的架构,为后来的员工持股制度埋下伏笔。
02
探索期:内部股制度的 “绑定实验”
1990 年,华为推出了具有开创性的内部股制度,彻底改变了股权的分配逻辑。当时华为将全部股权折算为等额股本,员工依据自身出资能力与入股意愿,以 “每股一元” 的标准认购;若员工离职,公司会按原认购价回购股份。
彼时参与持股的仅有 20 名员工,却实现了 “全员覆盖”—— 只要有意愿、有能力,就能成为企业 “利益共同体”。更关键的是分红机制:年度分红回报率常超 70%,部分年份甚至达到 100%,员工普遍会将工资、奖金及分红再度转化为入股资金。
这种制度的效果立竿见影:员工以 “创业者” 心态投入工作,有人连续一个多月驻守公司,有人因高强度研发导致视网膜脱落。正是这份凝聚力,让华为在 1994 年从 “代理商” 转型为 “自主研发企业”,当年销售收入达 5.5 亿元;到 1997 年,营收更是飙升至 32 亿元,3 年翻了 6 倍。
03
规范期:内部股的 “合法化升级”
1997 年,华为已成为国内通信设备行业的领军者,计划向国际化迈进。但此时的华为面临一个难题:员工从 20 多人增至 6000 多人,组织规模膨胀导致管理混乱,而早期不规范的内部股也亟需调整。
恰逢深圳市发布《深圳市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持股试点暂时规定》,明确 “内部员工持股需由公司工会持股会集中管理”。华为顺势推进股权改制:先是将企业性质从集体制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,再于 1997 年 7 月通过《深圳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规定》,明确 “入股自愿、股权平等、收益共享、风险共担” 的原则 —— 员工配股额由人力资源委员会审批,可少购但不能多购,股东会则以 “持股员工代表会” 的形式召开,确保决策能反映员工意愿。
同年 12 月,任正非等 777 名员工发起设立深圳市华为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,形成新的股权结构:华为新技术公司持有华为技术公司 5.046% 股权,两家公司的工会分别持有 33.086% 和 61.868% 股份。这次调整,让华为的员工持股制度彻底 “合法化、规范化”,也为后续的高速增长奠定基础 —— 到 2000 年,华为销售收入增至 160 亿元,3 年再翻 5 倍。
04
转型期:虚拟股票期权的 “危机应对”
2001 年,网络泡沫危机席卷全球,通信设备行业陷入低迷。但任正非的判断是 “反周期出击”—— 趁行业巨头收缩战线时扩大市场,而要实现这一目标,需要更灵活的激励机制,也需要符合潜在的上市要求。
华为聘请国际咨询公司韬睿设计方案,将原来的内部股改造成 “虚拟受限股”,核心规则是:员工无需出资即可获得期权,分 4 年行权;行权时,可选择按授权价购买虚拟股,也可直接兑现当年的价格差价。为了让员工与企业共渡难关,这一年的期权增发比例高达 20%。
这次转型,标志着华为的股权激励从 “直接持股” 转向 “契约式激励”,既保留了 “利益共享” 的核心,又增强了股权结构的灵活性。
任正非持股变化的关键节点:稀释背后的 “控制权逻辑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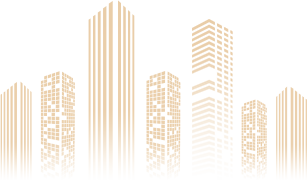

从创业初期的 “均等持股” 到如今的 0.52%,任正非的股份持续稀释,但这并非 “失去控制权”,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实现 “以少控多”,三个关键节点尤为重要。
01
2000 年:独立股东地位的 “首次确认”
2000 年,华为董事会做出两项关键决策:一是将华为新技术公司工会持有的 11.85% 股权并入华为公司工会;二是将任正非持有的 3500 万元股份单独拆分,在工商局完成注册登记。最终,任正非单独持股 1.1%,剩余股份全部由华为公司工会持有。
这一调整的意义远超数字本身:它标志着华为从 “集体持股” 转向 “创始人 + 工会” 的现代治理结构 —— 任正非的股东身份得到法律明确,避免了早期集体持股的模糊性;同时,工会持股确保员工利益与企业发展绑定,形成 “创始人主导、员工参与” 的平衡。这种架构此后从未发生根本性变化,成为华为股权的 “基础框架”。
02
2004 年:持股降至 1% 的 “战略选择”
2004 年,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华为控股与任正非,任正非的持股比例进一步稀释至 1%。从 1.1% 到 1%,绝对数值差异不大,但背后是华为的战略考量:随着业务扩张,企业需要通过增资扩股获取发展资金,而任正非主动将更多股权空间让给员工、用于企业发展。
这一变化,是 “财散人聚” 理念的直接体现任正非不追求 “股权数量”,而是通过 “分享股权” 凝聚更多人。此后,无论华为经历多少次增资,“任正非 + 工会” 的持股结构仅做小幅调整,始终保持稳定,为企业长期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。
03
2025 年:降至 0.52% 的 “历史延续”
2025 年的最新工商变更,延续了任正非股份稀释的趋势。由于公司注册资本增加 58.1 亿元,而他的出资额未变,持股比例从 0.58% 降至 0.52%。
这一变化看似被动,实则是华为股权逻辑的 “必然结果”:多年来,华为始终通过 “增资扩股” 支持业务发展(如研发投入、市场扩张),而任正非的股份不随增资增加,自然会被稀释。但这种稀释从未影响他对企业的掌控 —— 因为工会持有的 99% 以上股份,其表决权通过制度设计与创始人意志保持一致,实现了 “收益权共享、控制权集中” 的平衡。
股权稀释的深层逻辑:华为治理的 “三大支柱”

任正非股份的持续稀释,不是 “被动让步”,而是华为主动设计的治理体系,核心支撑是三大逻辑。
01
“财散人聚”:文化驱动的利益绑定
任正非的核心管理哲学是 “资源终会枯竭,唯有文化能永续传承”,而股权稀释正是这一哲学的落地。他仅保留极少股份,将 99% 以上的股权通过工会与员工共享,本质是 “用利益绑定人心”—— 员工不再是 “打工者”,而是 “企业所有者”,有动力为长期发展拼尽全力。
这种模式的效果很直接:华为能在 30 多年里保持高强度研发、应对外部压力,靠的就是 “全员共担” 的凝聚力。正如华为内部所言:“把股份分光,不是失去控制,而是用共同利益搭建更稳固的组织。”
02
虚拟股权:创新的 “激励与控制平衡术”
华为的虚拟股权制度,是股权设计的核心创新。截至目前,华为虚拟股总规模达 134.5 亿股,超 8 万名员工持股(占总人数 45%),但这些股权并不体现在工商登记中,而是由工会统一代持 —— 员工持有的不是 “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”,而是 “契约约定的收益权”(如分红、股价差价)。
这种设计的妙处在于 “两全其美”:一方面,员工能通过虚拟股分享企业利润,激励效果直接;另一方面,股权的表决权集中在工会,而工会的决策与创始人意志一致,确保任正非能掌控企业方向。既避免了 “股权分散导致的决策低效”,又实现了 “大规模激励”,堪称 “激励与控制的平衡术”。
03
现代企业治理的 “中国实践”
在西方企业治理理论中,“股权集中度” 与 “控制权” 通常呈正相关 —— 持股越多,控制越强。但华为打破了这一常规:任正非仅持 0.52% 股份,却能有效掌控企业,靠的是 “中国化的治理设计”。
核心在于 “控制权与收益权的分离”:员工通过虚拟股获得 “收益权”,而 “控制权” 通过工会持股集中 —— 工会作为持股平台,其决策机制确保了创始人的核心地位,同时又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(如员工持股需通过工会管理)。这种模式既借鉴了国际企业治理的经验,又贴合中国的制度环境,成为 “中国式现代企业治理” 的典型案例。
华为股权设计的启示:企业长久发展的 “三大关键”

华为的股权之路,不仅是自身的探索,更为其他企业提供了三大启示。
01
激励机制:要 “大规模” 更要 “动态化”
传统股权激励常陷入 “激励范围窄、效果递减” 的困境,而华为的突破在于两点:一是 “大规模覆盖”,将近半数员工纳入激励,让更多人成为 “利益共同体”;二是 “动态调整”,股权分配随员工贡献变化,避免 “一劳永逸” 的惰性。
数据显示,华为员工年收入(工资 + 奖金 + 福利)是股东分红的 3 倍,“劳资比例 3:1” 的分配结构,确保了员工能分享发展成果。这种 “动态、普惠” 的激励,才是企业保持活力的关键。
02
企业治理:要 “国际化” 更要 “本土化”
华为的股权设计没有照搬西方模式,而是结合中国政策(如工会持股规定)、企业实际(员工规模大、需集中决策),走出了 “本土化” 道路。比如通过工会代持解决员工持股的法律问题,通过 “创始人 + 工会” 的架构平衡控制与共享。
这启示其他企业:治理模式没有 “标准答案”,关键是贴合自身所处的制度环境、业务特点,找到 “合规性与有效性” 的平衡点。
03
发展理念:要 “短期利益” 更要 “长期主义”
任正非股份的持续稀释,本质是 “长期主义” 的选择 —— 不追求短期的股权收益,而是通过分享股权,构建能支撑企业长久发展的 “利益共同体”。正是这种理念,让华为能在研发上持续投入(多年研发占比超 15%),在行业低谷时 “反周期出击”,在外部压力下保持团结。
对企业而言,短期的利润增长或许靠市场机遇,但长期的竞争力一定靠制度设计 —— 华为的股权实践证明,“让更多人受益的制度,才能支撑企业走得更远”。
从 1987 年的 2 万元注册资本,到 2025 年的 638.9 亿元注册资本;从六人均等持股,到任正非持股 0.52%—— 华为的股权演变,是一部 “以股权为纽带,连接人、企业与长期发展” 的治理史。任正非的股份稀释,不是 “权力的退让”,而是 “智慧的分享”:通过 “财散人聚” 的理念、虚拟股权的创新、本土化的治理设计,华为既保持了决策的高效,又激发了全员的活力。
对当下的企业而言,华为的启示或许是:真正优秀的治理制度,不是 “掌控所有利益”,而是 “让更多人创造并分享利益”—— 这才是企业穿越周期、持续成长的核心密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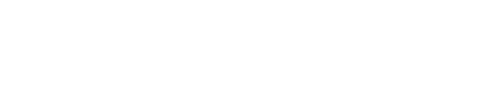
智合商学ZHIHESHANGXUE
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